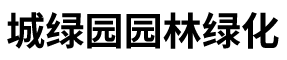安博全站App下载安装/知识
温州人为什么喜欢榕树?
温籍散文家林斤澜在散文《榕》中这样回想八字桥的大榕树:“枝叶盖着河,河上的桥,过街,盖住周围的店面大树底下好乘凉,也好做市、做阵、做会、做热烈,大树底下成了活动中心。”
温州是一座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,水网布满、河道纵横。温州水乡与绍兴、姑苏等江南水乡,又有少许不同,最显着的差异便是小桥流水、村头路口那一棵棵遮天蔽日的大榕树。温州地处榕树植物圈的最北部,瓯江以北,除了温溪镇古榕群外,稀有榕树的身影。
矗立在温州城区、各个乡镇的“路中榕”,既是一道共同的景色,也是温州人爱榕的实证。温州人甘愿抛弃宽阔垂直的大街,绕行在路中心一株株大榕树身畔,市中心信河街、八字桥、南塘天桥、马鞍池东路、望江路路中心的大榕树是温州人一眼认出家园的指示灯。
烈日炎炎,一路循着阴凉的榕树树阴回家;或是傍晚时分,在村头桥边大榕树下纳凉,是许多温州人夏天最美的乡愁。
温州人爱榕,也展现在历代温州文人笔下:南宋学者薛季宣的《大榕赋》,和李纲的《榕木赋》,是我国文明史上稀有写榕树的两篇名赋,被收录在清人陈元龙编纂的《历代赋汇》中。
榕树是我国南边常见乔木,散布在浙南及江西以南区域,尤其在福建、广东等一带广为培养。
榕树四季常青,树形特异。成年榕树常有从树枝上向下成长的垂挂“气根”,落地入土后成为“支柱根”,柱根相连、柱枝相托,构成独木成林的共同景象。
早在晋代,嵇含的《南边草木状》中,已记载其时南边区域遍及培养榕树:“榕树,南海、桂林多植之,叶如木麻,实如冬青,树干拳曲其荫十亩,故人以为息焉。”北宋时期,福州开端很多栽植榕树,《和平寰宇记》载,“榕其大十围,凌冬不凋,郡城中独盛,故号榕城”。
榕树也是温州的乡土树种,在12个县(市、区)都有散布。温州全市百年以上树龄的榕树逾越1000株,数量逾越福州的895株。
1985年,温州展开市树市花评选活动,小叶榕从黑松、樟树等候选树木中锋芒毕露。除温州外,福建福州、江西赣州、广西柳州、台北等城市都以榕树为市树。1997年,福建省还把榕树作为省树。温州也是我国最北以榕树为市树的城市。
其实,樟树比榕树更早、更多地见诸温州史料记载。如宋代沈括《梦溪笔谈》中,就说到“温州雁荡山,全国奇秀祥符中,因造玉清宫,砍木选材,方有人见之。”学者考证此次砍木砍的多是樟树。在此之前,三国时期孙吴在平阳建横屿船屯,学者觉得也与周边盛产造船用的豫樟有关。2007年平阳鳌江还曾挖出沉埋千年的香樟木,有专家估测或许便是其时运至横屿船屯的宝贵木材。
樟树可作造船、修建等质料,有药用价值,还能制造樟脑、樟油,可谓浑身都是宝。但也正因而,樟树被很多采伐。相比之下,被古人视作“不材之木”,不能成材不能烧火的榕树,却获得了成长空间。
在明代弘治《温州府志》中,所载温州特产木类有“松、杨、桧、柏、桂、栎、槐、榆、榕、枫、桑、杉、樟、桕”,并着重“产之独土所宜者,曰豫樟与棠。”这说明在明初,温州的古木以樟树、棠树为主。相隔两百多年后,清乾隆《温州府志》中,樟树位置下降,榕树后发先至:“木类:松、五粒松、倒生松、榕(邵公屿有榕树盘郁,其上清荫数亩)、樟、桧、杉。”
此外,榕树在温的优势位置,与唐宋之后温瑞塘河流域的开发有关。塘河流域地形陡峭、水网密布,古人经过舟船等交通工具出行,不易辨识方位。以巨大的树木为地标,便是一种挑选。三垟吕家岸村的樟树和枫树组合,三垟张严冯村水莲宫的水中榕,都是有名的航标树。榕树树高冠大、易培养、成长快,还有樟树不能够比较的成阴才能,因而便大放异彩,在温瑞塘河流域获得绝对优势。
温瑞塘河流域平原水网地带,是温州榕树散布最多区域,简直每个村庄的村头路口都有榕树。据统计,温瑞塘河流域共有63株古榕,其间500年以上的有36株。
这是清代诗人方鼎锐,乘坐夜航船,从温州城区经温瑞塘河到瑞安(章安)时沿途看到的景色。
脱离浙南的温州,再往北的水乡,就鲜有“夹岸榕阴”的景致,这也是温州水乡差异江浙其他水乡的共同之处。
除了塘河沿岸,温州各地都有许多与榕相关的共同景象,江心屿便是最为闻名的一处。江心屿谢公亭旁的“樟抱榕”,樟树与榕树的树龄别离逾越1300年、500年,是国家一级名木古树,还被演绎出《高机与吴三春》的经典桥段。江心东塔塔顶的百年古榕、榕树园,也是榕树名景。
北宋温州知州杨蟠写有一首《翠幄轩》诗:“海榕树倒出,皮斡亦轮囷。或问寿几何,千年为一春。”《孤屿志》中记载,龙翔寺中有翠幄轩,为宋高宗驻跸处。可见千年之前,江心屿古榕就已经是一大奇迹。
清同治年间,温州府同知郭钟岳在《瓯江小记》中,记载了城区东山下茶场庙“五连理树”奇景:“跨桥枕水,五树连理而生,皆榕树也。”
在唐代之前,或许由于浙南、闽粤区域地处偏僻,榕树鲜见于文学创作中。直到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柳宗元被贬至柳州,一句“山城过雨百花尽,榕叶满庭莺乱啼”,让榕树成为具有南边特征的景象代表。尔后,历代诗人对榕树题咏不断,苏轼、陆游、杨万里等都有咏榕诗。
温州人丰厚了榕树所代表的思维内在。南宋永嘉学派创始人薛季宣的《大榕赋》,是描绘榕树的名赋。薛季宣把榕树之材用与德义联系起来,以为它德义兼备,“不以直节为高,不以孤生为异。凌寒而不改其操,连理而不称其瑞。”
榕树因其庇荫广大的特性,还被赋予仁德、容纳的意蕴。自薛季宣后,榕树被比德正人,不少文人纷繁以榕树命名字号、斋室、文集等,使得榕树有了更深入的精力和文明内在。如晚清瑞安学者、官员胡调元取字“榕村”;晚年隐居九山河畔、古榕旁的曾衍东,将居住温州所作的诗歌集取名为《古榕杂缀》。
榕树与温州人的日子场景严密相连。郭钟岳用一首《瓯江竹枝词》中描绘时人夏天日子场景:“榕树联街好纳凉,楮纱裁作夏衣裳。芭蕉叶大绿当户,丁冬花开红过墙”。清同治十一年(1872)春,闻名学者俞樾从杭州前往福宁,自平阳坐小舟行三十里,至钱仓,沿途博览南雁荡美景。他在诗中所描绘的温州美景中就有榕树:“榕树阴中曲曲堤,直从萧渡到琳溪。”
榕树作为温州的市树,以扎根土地、坚强成长著称,是温州开辟、务实精力的标志。正如当年温州市人大在命名榕树为市树时,说到它“能反映温州天然面貌和温州公民生气勃勃,奋发向上精力,有利于激起公民爱国爱乡之情”。
半个世纪前,这个小城一过傍晚就墨黑。我老屋在百里坊,从大街回家要靠耳朵,听见碎叶声,那是坊口了,朝黑洞洞里转弯便是。坊口有一株榕树,两人抱不过来,不知多少年岁,我父亲就听着碎叶声朝黑洞洞转弯的。
坊口到我家老屋,不过三四百米。从老屋再走一二百米,是个三岔路口。原先街边都有河,有两条桥像八字搭在三岔河上。这儿就叫做八字桥。八字桥中心,又是一株大榕树,两人不能合抱。枝叶盖着河,河上的桥,过街,盖住周围的店面。大树底下好乘凉,也好做市、做阵、做会、做热烈,大树底下成了活动中心
少年离家,约四十年后回故土看看,河填了,桥平了,只要榕树仍旧,没有长粗,也不显衰老,如同这一把年月还不行个零头。我是依托榕树,找到了老屋的门台。